| 文學獎-陳瑞麟(陳列) | 文學獎-賴香吟| 藝術獎-曾道雄 | 藝術獎-謝三泰|
賴香吟 – 專訪.評定書.得獎感言
霧濃深重,提一盞燈前行——賴香吟的寫作之路
採訪撰文/林欣誼
 身為一個寫作者,與一個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角色,對賴香吟來說,都是「絕對性」的——前者面向「絕對的精神世界」,後者則是「絕對不講道理的現實」,「這兩者不太溝通,但同時存在我生活裡。」
身為一個寫作者,與一個在婚姻與家庭中的角色,對賴香吟來說,都是「絕對性」的——前者面向「絕對的精神世界」,後者則是「絕對不講道理的現實」,「這兩者不太溝通,但同時存在我生活裡。」
走過磕磕絆絆,如今的日子較之前安頓了。她平和地說:「寫作者被拋到現實生活固然很磨難,但也帶來一些正能量——讓我把景深拉寬,知道自己的經驗放到廣大現實裡,會有多少共通性,因而能在寫作材料的價值與揀選上,保持理性。」
二元的對立與平衡
德國的秋天已冷,旅居柏林的賴香吟,身穿針織厚衣,隔著遙遙的距離,談起生活,依然如此摩擦親膚;而寫作也仍如她一向所說,並非是救贖,「我不想扮演一個只為了救贖自己的作者,也不想讓自己的寫作變得私人且不可理喻地感性。」
天秤的兩端是寫作與現實,也是感性與知性。賴香吟回顧自年輕時代起,她就在這種二元分裂中深覺困惑,「如果我要當個文學人,不是應該把書架上的小說啃完嗎?但常吸引我閱讀興趣的,又是社科與哲學,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應該從事什麼。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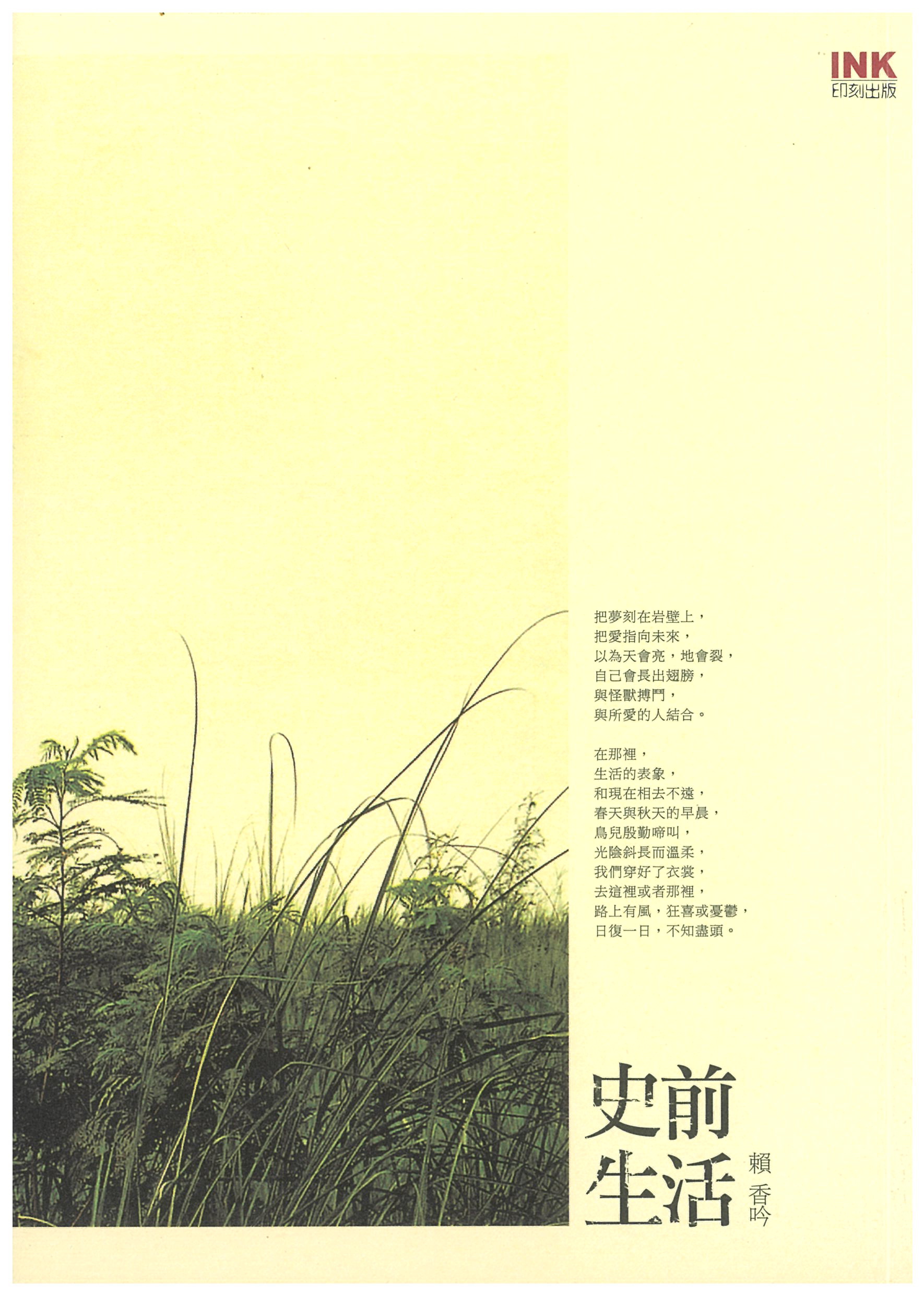
直到中年,她逐漸對這種衝突習以為常,「年少時很怕被寫作的網整個罩住,現在知道掙脫、或說分配的方法,找到兩者的平衡,甚至互補。」若說文學需要不斷被加寬、變得柔軟與豐潤,非文學就像靈巧的工具,去修整那團豐潤,從中提取合適的素材。「現在知性上穩了,我才比較『敢』讀文學作品了,文學給予我慰藉與滿足,也讓我對客觀的世界不要失去觀察的愛。」她自嘲地笑了笑,「雖然這樣說很俗氣,但真的就是,愛。」
生活從拉鋸到平衡,從粗礪到逐漸撫平,三言兩語所概括的,卻是她以烏龜般的緩慢姿態,徒手赤足、接地摸索的歷程。
賴香吟早在18歲便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〈蛙〉,30歲前後的世紀之交,接連出版小說《散步到他方》、《霧中風景》、《島》,但此後逾十年,她在應付現實生活中盡失力氣,幾乎放棄寫作,期間僅出版散文《史前生活》。
直到2012年的《其後それから》,以小說體裁書寫被亡者留下的人如何倖存走過,其後,她才感到被封口的路有些鬆動了,能夠再拾起筆,繼續打磨文字,也在日子的打磨後,心境平靜下來,「知道自己在人世間的身分是什麼,關於寫作這一行要有的技術、磨練與情懷,心裡有底了。」


2012年,以《其後》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,頒獎現場大合照(左圖,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)。
2012年,以《其後》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,頒獎現場與編輯合影。(右圖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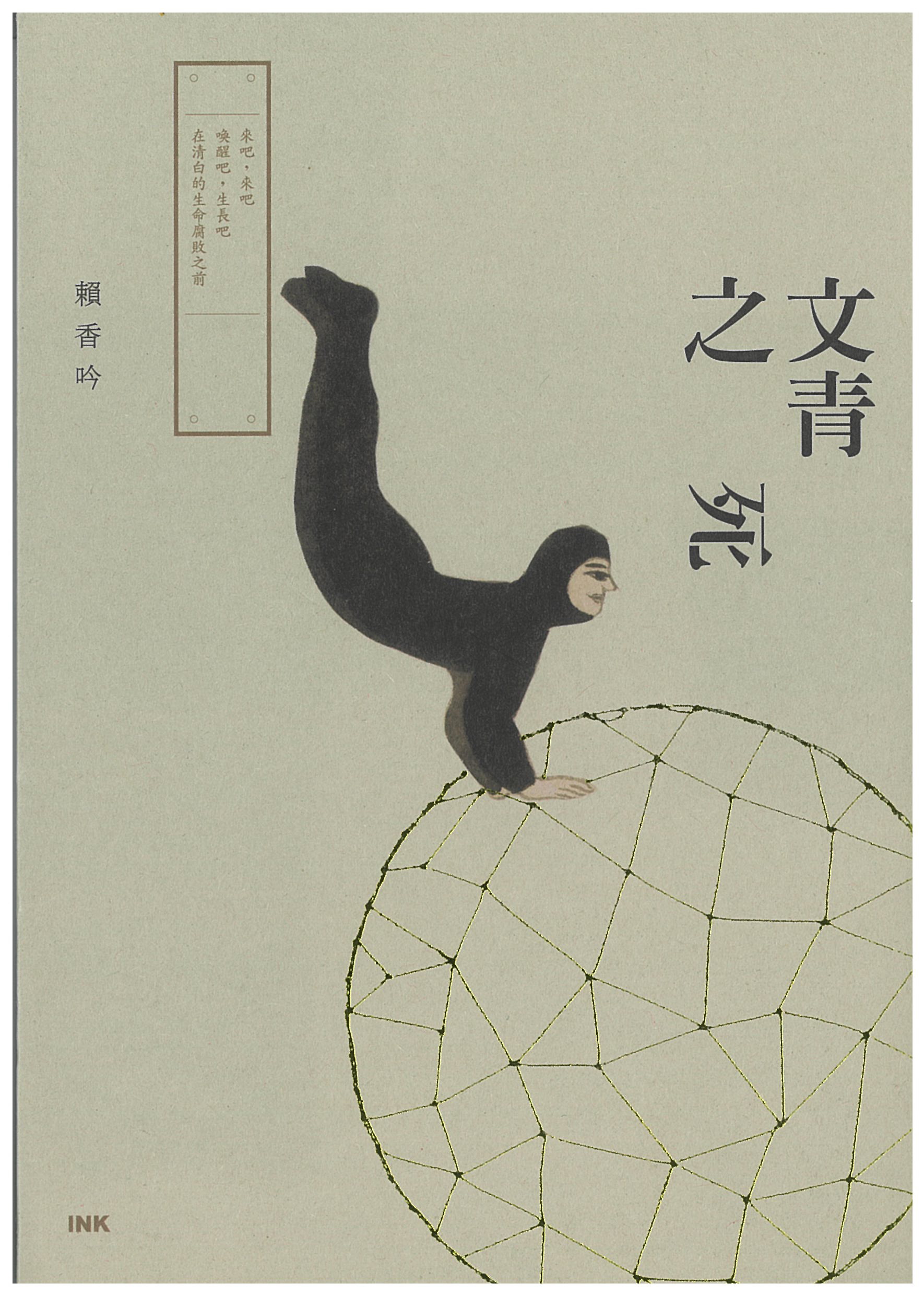

2022年,《島》的書店座談,台北飛地書店(右圖,聯合文學館提供)。
「文學路徑通常是殊途同歸,我們都是在追求一些方法,把這個想讓人逃走的世界、或是我們想回報給這個世界的東西,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。」[1]賴香吟曾寫過這段話,而現在,把「回報」拉得更遠來說,不只是從逃亡的路徑回返,說出那些曾經發生的事,更是「找到個人在時代中的位置,思考我們為何這樣生活,與時代之間的聯繫。」
這也是為何她認為,在寫作中「把時代感放進去」是必要的。如她近年來的作品,《文青之死》描繪她同代人的浮世眾生、婚姻與生活;《翻譯者》(後因版權問題銷毀,大部分篇章收入新版《島》)多著墨90年代,重編出版時,她自言「腦中對90年代的關鍵字是『解嚴的未完成』」[2];《天亮之前的戀愛:日治台灣小說風景》融合她對日治時代作家的研究;去年新作《白色畫像》的時空則交織落在白色恐怖時期。作品橫跨各年代,而每一本書的寫作時間跨度,也都超過十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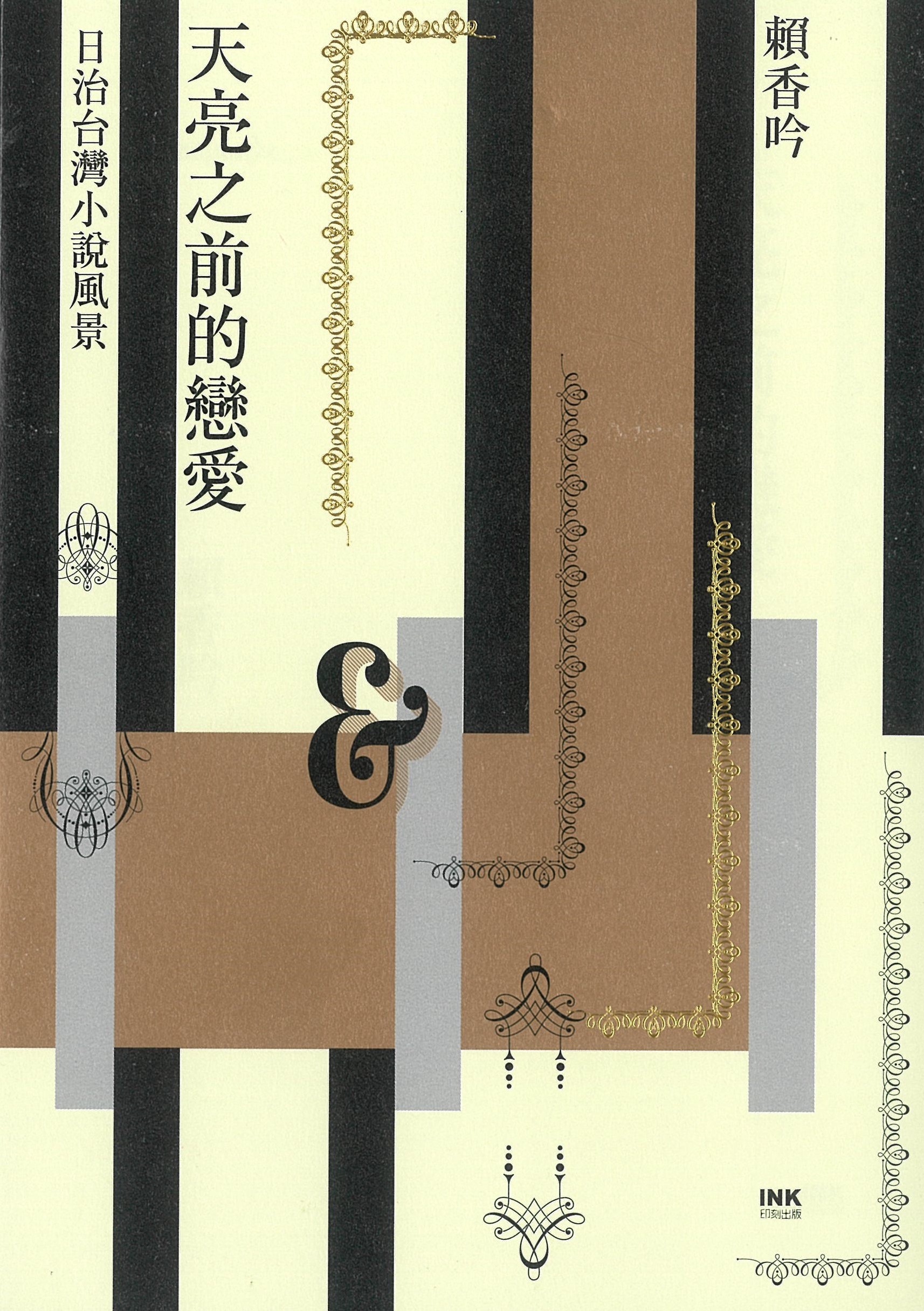

2019年,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文學館演講(右圖,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)。
《白色畫像》分別描寫三個人物,筆調輕淡而綿長,其或被理解為「白色恐怖文學」,對此她表示:「我不特別否定,但這是因時代的需要去取用作品,非作品為了時代的需要而寫。」然若能夠,她更想稱之為「描寫戒嚴時期下的日常生活」,並以「被治理的民間階層」取代「大時代下的小人物」說法。
學者范銘如曾觀察指出,賴香吟過去的小說不易進入,但這種隔閡感在《白色畫像》消失了,感覺作者與小說人物站到了一起,從「隔」到了「不隔」[3]。賴香吟解釋,早年因感受到解嚴後,社會上洋溢一種重新去敘述本土故事的飽滿情緒,充滿熱情希望,「在我當時緊張的天秤上,覺得感性太強,就會在知性面發作,因此身為小說家看待筆下人物的視角,也偏向懷疑。」
而今,內心的天秤兩端比較和平了,能夠理解當時的社會,是基於長期壓抑後的反彈,也懂得更多人世間普遍的道理了,所以現在,壓抑放鬆了,懷疑也退散。但與其說她為人物畫像,毋寧說角色自有生命力,而她除了史料的研究與取材,更以一種作家感官性的同理,讓他們活著,感受,並呈現時代的情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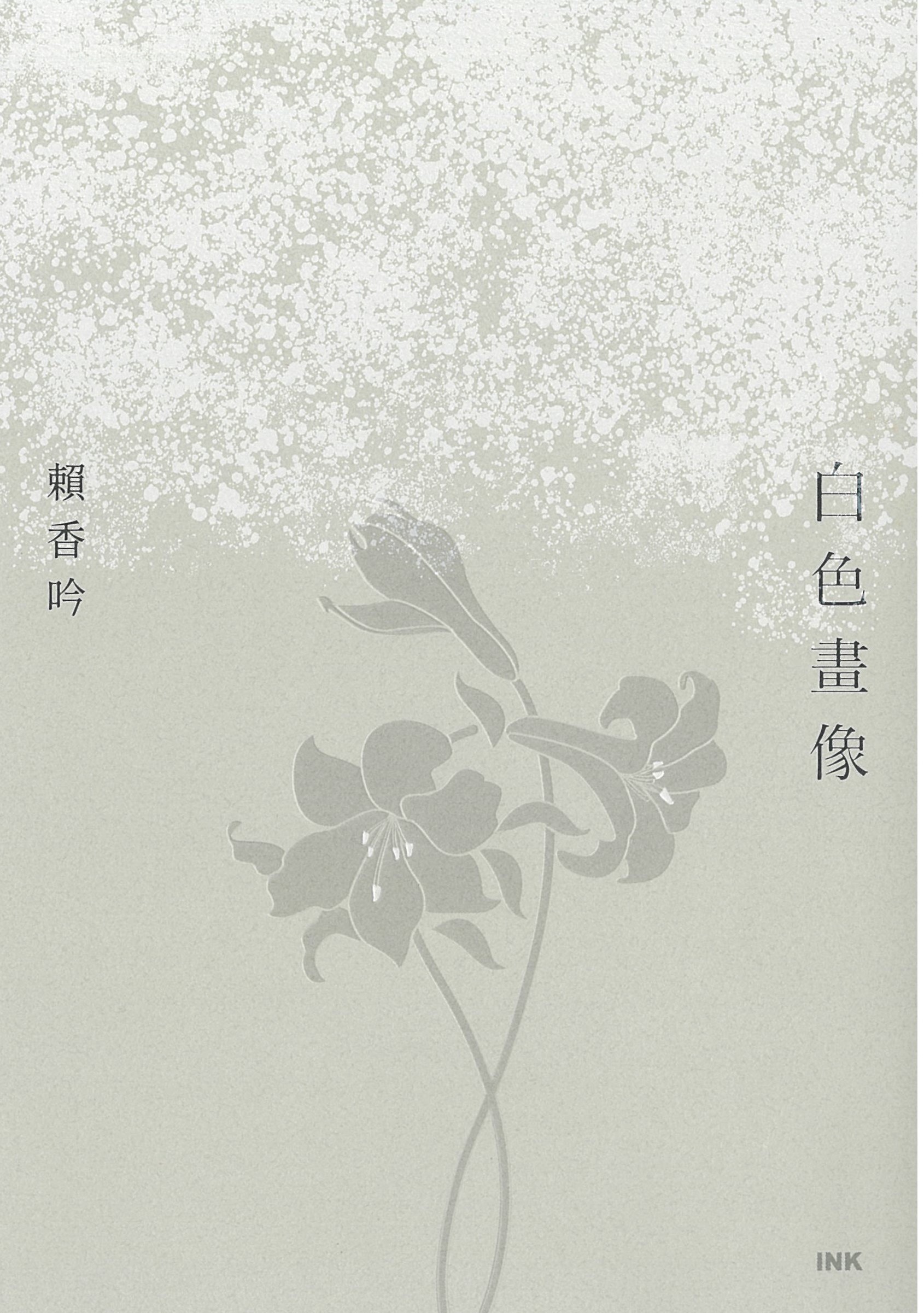
 2022年,以《白色畫像》獲台灣文學金典大獎(右圖,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)
2022年,以《白色畫像》獲台灣文學金典大獎(右圖,國立台灣文學館提供)
《白色畫像》橫掃各大獎項,標誌了賴香吟小說的新高度。但她並未停下腳步,目前著手的寫作,一為《文青之死》某部分的延伸,「想把屬於我這代人的經驗與領悟,透過文學表達出來,並特別專注在女性的成長,尤其是我們的『社會化』與『情感經驗』」。
她觀察道,從前幾年林奕含書寫《房思琪的初戀樂園》,到今年的Metoo運動,關於「女性對情感和自身身體的規範與認識」漸漸浮出成為議題,並呈現了女性在承受和表達上的世代變化。「我們這代所謂的知性女性,遭遇到的往往不是帶著玫瑰色的理想過程,而是充滿險惡與虛偽,但除了少數如李維菁寫得較猛,其實我們不太敘述、甚至自我消解敘述的必要,也沒有結盟的支援系統可言。」
「『我們這代人』聽起來很普通,每一代不都是從青春到老衰?」她說,但現在感覺能寫了,是因為預感到「我這代女性的特質正在消失。而這不是壞事,是好事。」她強調。
與此同時,她開啟的另一書寫領域,則延續《天亮之前的戀愛》對過去時代中人的「同理心」,藉由她生活在德國的切身當下、對每日接觸人事物的觀察,重讀並重新領會這裡與周遭國家的歷史與文化,「我發現,台灣對二戰後中東歐國家的理解非常少,但他們和台灣有許多共通之處,因此我希望能夠用文學的方式把它『接起來』。」
給花讓它盛開的時間
面對提問,賴香吟總是皺著眉頭思索,慢慢答以精準與廣闊。這何嘗不也像她的寫作,盡可能走進那一團時代的迷霧,「霧濃深重,人與人的形影面目,經常遮蔽而模糊」[4],而寫作者的任務,就是從中抓到個人與時代的共感,並將它提到精妙的敍述層次。那樣艱難的思考,情感的共鳴,與寫作技藝的不斷雕琢,不正是文學本身?
 人生來到「後中年」,她更理解寫作是場馬拉松,或借用薩伊德「晚期風格」的概念譬喻,作家需要成長與成熟,就像為植物澆灌水與養分,花終會開,但需要時間。因此,她對台灣寫作環境最殷切期望便是,每個作家的生命史能更拉長,「希望不論讀者、社會或寫作者本身,都能辨認出時間的捉弄,而能突破限制,把寫作的生命、對文學的認識往後拉長與掘深。」
人生來到「後中年」,她更理解寫作是場馬拉松,或借用薩伊德「晚期風格」的概念譬喻,作家需要成長與成熟,就像為植物澆灌水與養分,花終會開,但需要時間。因此,她對台灣寫作環境最殷切期望便是,每個作家的生命史能更拉長,「希望不論讀者、社會或寫作者本身,都能辨認出時間的捉弄,而能突破限制,把寫作的生命、對文學的認識往後拉長與掘深。」
從文學史來看,每一代都有活躍的作家,但她更盼望能長期看到「作家是不死的」,不要停止思考,也不要忘記自己在乎的價值,在這一條路持續走下去,如此才能為後面世代打氣,「就像提一盞燈在前方,後面的人或許不會立即回應,但以後,他們總會看到的,這就是一個國家與文化的河流。」
就像賴香吟的寫作,從來不快,耐心恆長,因為前方總是霧濃深重,「我希望知道後面有什麼,所以我還在路上,我會繼續走。」
[註]
[1] 引自賴香吟X莊瑞琳對談,〈一個半徑很大的零〉,《春山文藝》第二期。台北:春山。2020年9月。
[2] 同上。
[3] 引自林文心,「賴香吟《島》新書分享會:前史與再生」。Openbook閱讀誌。2022年8月17日。https://www.openbook.org.tw/article/p-66705
[4] 引自賴香吟,《白色畫像》後記。台北:印刻。2022年1月。
